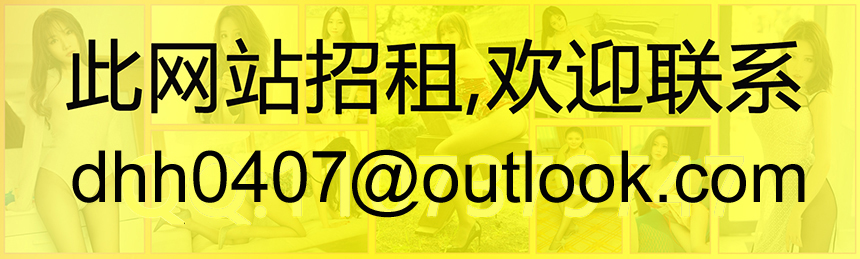当我们厌恶烂梗时,毕竟在厌恶什么?
迩来,《长安三万里》火极了,家长们带着娃在影戏院背诗,惹起了广泛讨论。与之构成镜像的,是对小孩说“烂梗”的厌恶心情,也是一波比一波凶悍。
试想一下,假如唐诗三百都城换一种表达,那我们今天看到的,就不再是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“百尺竿头九万里”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“两岸旌旗绕碧山”,而是“汪伦是我真铁子”“我给贵妃做颜粉”“庐山瀑布炸裂了”“剑外忽传收蓟北,谁懂啊家人们我哭死”……
《长安三万里》里有诗性,诗是言语的最高等别,优雅、优美、丰厚、神韵绵长。前些天刚刚过完100岁生日的叶嘉莹教师,有一名句:“诗歌最大的作用,就是要让你有一颗不死的不僵化的心灵”。而“烂梗”则处在言语的下沉方位,充溢偏反复、夸大、随声赞同,它会让人患上“笔墨失语症”。
当我们厌恶“烂梗”,毕竟在厌恶什么?说“烂梗”,还得从“梗”本身聊起。
“梗”有三重涵义,一为植物的茎,一为笔挺,一为拦阻,哪个都和网络用语不关。由于它在“烂梗”中的使用,但是是个讹字,原本应该是“哏”,意思是幽默幽默,譬如“你这人真哏儿”,天津就被称为“哏都”。以前无从考据,毕竟是谁第一次用错了这个字,但久而久之、以谣传讹,就有了“梗”这个古代人基本绕不开的文明征象。
梗像言语中的“预制菜”。拿来加热就能吃,当用梗表达时,就不会再有人追查鱼香肉丝里毕竟放青笋丝照旧干笋丝,红烧肉毕竟用绍酒煨照旧啤酒煨,历程和因由都变得不再紧张。
玩梗并非是网络年代的特产。梗的紧张,在于心心相印,以是它总是和“Get”搭配,用只言片语转达多量信息,道上“黑话”、文人用典、乡下俚语,都能算是各自圈内的梗。
网梗同理,能精准撞上众人的奇妙心情,加之网络自带的转达力,很快就能走完普及、使用、多量复制等几个阶段。但梗用过多就烂,网梗一旦开头偶然义反复,就被打入了“无内在、偶然义、无咀嚼”的“三无”烂梗步队。好比以前的“蓝瘦香菇”“yyds”“你个老六”……如今看来是云云老土、无聊,令人厌恶。
我们对梗的忠实度,约莫还不如宫斗剧里“渣皇”对宠妃来得更久。
梗自有其生命周期。好梗能跨时空传播,在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的年代,《诗经》成为春秋年代的交际梗百科;春秋的董狐秉笔挺书,直到清代仍有诗云“直笔何人继董狐”;烂梗则会静静退隐,诸如“奥利给”“耶斯莫拉”日渐退去人们的语料库。
但是,有些烂梗分明不知所云,“超发”用滥了,仍在充任交际货币,好比“我giao你个giaogiao”,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此中,夸大式“烂梗”是重灾区。“栓Q”“真的会谢”“依托争辩”原本还几多带点心情、有点别致,可用多了跟“啊哦”之流没什么分散,让人生厌。最典范的是“666”“yyds”“绝绝子”“太炸裂”“神仙XX”等,每个梗盛行之后,就会显现更分量级的新梗来代替,用语越来越夸大,又从夸大归于平庸,一块演化,层出不穷。
当梗被经常使用,必会遭遇语义磨损,即贬低。当“yyds”从十分的称赞,变成普平凡通的“好”,乃至只是单纯的叹息后,烂梗也就随之诞生。
对此,费孝通的师兄,中国早前社会学家李安宅在1946年提出“言语通货变大”的看法,指“言语与其眼前的头脑、心情的不婚配”。事先,他以此挖苦时人滥用“救国”,随声赞同地喊“德谟克拉西”等大词,主张语言不要“灌水”。只是,事先的他很难想到,网络年代的烂梗能云云言之无物,一句话里只剩下“水”。
我们厌恶孩子说烂梗,是由于孩子正处于言语培基阶段;厌恶媒体用烂梗,是由于他们理应具有更高的笔墨输入水平;偶尔,我们乃至厌恶本人用烂梗,由于那种启齿忘词的以为的确很堵心。
分明很厌恶,但却离不开。这就是今世人对“烂梗”的奇妙以为,它具有某种古代病的典范表征——盛行化、交际化,平凡人被裹挟、被塑造,不晓得该怎样办。
倒也不必太过焦急。人们对“烂梗”的入侵,并非毫无防备、大开城门,关于“笔墨失语”的讨论不休都在举行,对小孩最少不应该说“烂梗”的共鸣,也以前告竣,媒体用了“烂梗”,会被受众挖苦讪笑……这些都证实,在制造烂梗、使用烂梗之后,我们也在反思烂梗、警惕烂梗,社会的全体言语定力、表达定力都有所提升。
就像开头所说的,《长安三万里》同时劳绩口碑与流量,恰好证实诗与美是不会被打败的。劣币摈除良币时,良币也会摈除劣币,在笔墨江湖,能传播千古的,向来都是《唐诗三百首》,而不是《烂梗三两句》。
(央视网微信公号)